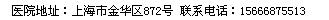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淋巴管瘤 > 病因探寻 > 37分Nature子刊的重磅综述刷新你对
37分Nature子刊的重磅综述刷新你对
转移性肿瘤的基础研究进展和临床治疗介绍
关于转移性肿瘤的机制和临床治疗,一直都是个长盛不衰的话题。上一期,我们在《肿瘤转移的百般花样儿,都逃不过这篇顶刊重磅综述的火眼金睛!》的推送里给大家介绍了肿瘤转移过程中的代谢。
年1月13日,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KarunaGanesh和JoanMassagué教授在影响因子36分的《NatureMedicine》上发表了题为《Targetingmetastaticcancer》的综述长文,为我们系统性的介绍了关于如何治疗转移性肿瘤的临床和基础研究进展。
JoanMassagué教授早期就发现了TGF-β抑制和促进肿瘤细胞生长的双重作用,并在CNS顶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肿瘤的转移机制研究非常深入。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吸收综述的内容,榨干其每一滴精华,本工在阅读综述的时候,也给大家翻译了遍,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有真正价值的“学术营养”。
摘要
近年来人们在癌症治疗方面取得了进步,但转移仍然是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最近的研究已经发现了转移起始细胞的独特生物学,它可导致肿瘤在远处器官中生长,逃避免疫监视和选择转移微环境。在本文中,我们回顾了关于微转移和大转移(macrometastases)的治疗进展方面的进步和成果。这些见解是从肿瘤测序、机制研究和临床试验(包括免疫疗法)中获得的。这些研究揭示了转移的起源和性质,并确定了开发更有效的策略来靶向转移复发和改善患者预后的新机会。
引言
超过90%的癌症死亡是由转移引起的。与通常可以通过局部手术或放疗治愈的原发性肿瘤不同,转移是一种全身性疾病。因此,包括筛查、化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在内的全身治疗是预防和治疗肿瘤转移的主要手段。近年来,改善癌症治疗效果的共同努力也取得一些成果。
年至年,美国癌症死亡率下降了29%,至年间年均下降1.5%。在转移性黑色素瘤(?6.4%)和肺癌(?4.3%)中观察到的降幅最大,这主要是由于免疫疗法的变革性影响。在转移性乳腺癌中,检查点免疫疗法的效果较差,但已经批准了几种新的靶向治疗,被诊断为复发的患者的中位5年生存率从年的18.4%(95%可信区间,13.6-24.8%)增加到年的32.6%(95%可信区间,20.6%-51.4%)。
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但包括胰腺癌、肝癌、子宫癌和肉瘤在内的几种癌症的死亡率都停滞不前或上升,绝大多数任何类型的复发或新发转移癌患者在确诊后5年内仍会死亡。因此,治疗转移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基础肿瘤学和临床肿瘤学的进步是进一步提高转移性癌症治疗水平的关键。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肿瘤生物学家和临床研究人员之间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合作。技术进步使得快速积累包含疾病进展和药物反应信息的肿瘤基因组数据成为可能。有越来越多的临床试验包含了大量的实时生物样本收集和患者特异模型的产生,包括治疗前、治疗期间和耐药性发展后患者来源的移植瘤和类器官。创新性的试验设计(例如篮子、雨伞和平台试验)缩短了将药物带入临床所需的时间。
这些方法使研究人员能够灵活地识别治疗反应的生物标记物,在体外模型中验证耐药性机制,并开发下一代药物。从这个过程中所得到的丰富的数据集产生了关于转移的潜在机制的假设,然后可以在功能实验中进行测试。因此,临床前研究和临床后研究之间的相互作用促进了对转移生物学的理解,促成了新治疗方法的开发。目前的研究目标是开发新的治疗方法靶向转移的休眠阶段中转移播种、休眠和微转移生长的单一(singular)生物学特征,并提高现有治疗方法对显性转移的疗效。在这里,我们将重点介绍一些最新的生物学见解,以及这些进展如何指向新的治疗机会,以改善癌症患者的预后。
肿瘤转移的起源和发展
虽然癌细胞扩散可以开始于肿瘤进展的早期,但大多数离开肿瘤的细胞受制于各种压力而无法在远处器官中定植。为了形成转移,癌细胞必须经过一系列以前被称为“转移级联”的步骤,每一步都需要特定的功能(图1)。通过作用于不同种类的癌细胞群体(cancercellpopulations),这些压力可以筛选出适合在远处器官定植的克隆。
1.肿瘤内异质性的来源
癌细胞群体的异质性不仅源于肿瘤内基因组的不稳定性和遗传变异,还源于恶性前体细胞具有多种表型变异的能力。干细胞样恶性前体细胞有能力流畅地(fluidly)采用不同的表型状态,以响应细胞的内在发育程序和外部基质信号。这种被称为表型可塑性的特性使癌细胞能够适应特定的微环境,克服转移障碍并抵抗治疗。表型可塑性加剧了基因组多样性癌细胞群体的异质性。癌细胞群体异质性的变化可能反过来影响肿瘤间质的组成,从而影响出现有转移复发倾向的癌细胞。
2.促肿瘤转移基因
结合了转移实验模型和患者的肿瘤基因表达数据的研究,已经确定了在癌细胞中表达可促进小鼠模型转移并与临床复发相关的基因。目前已发现很多基因有助于癌细胞的扩散,如侵袭、循环、外渗、抵抗基质和代谢应激、转移生态位的形成、器官特异性基质成分的共同选择以及其他促转移的功能。其中一些基因由原发肿瘤中的癌细胞表达,一旦扩散到特定器官,便启动细胞的转移。当播散性癌细胞适应特定的宿主组织环境时,其他促转移的基因发生明显表达。促转移的基因是抗转移治疗的候选靶点,其中几个也是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的对象。
3.驱动转移的突变(Metastasis-drivingmutations)
很多研究利用大型癌症基因组学数据集来识别有利于转移的突变。这项研究的指导原则是,肿瘤的恶性细胞群体在选择性压力下发生进化,以抵抗肿瘤进展的压力获得生存。原发癌和转移癌的突变模式和总体突变负荷基本一致,这一发现在对大肠癌、非小细胞肺癌、胰腺癌和肾癌等大队列的比较中得到证明。
尽管离散的亚克隆基因改变表明某些克隆具有顺序优势。癌症基因组学研究发现很少有复发转移相关突变,复发突变可能与转移性疾病的特定治疗耐药有关,而不是转移性级联进展的介质本身。在侵袭性肿瘤中,调节DNA甲基化和染色质修饰的基因经常发生突变,临床和实验性转移的研究表明获得性表观遗传和转录改变是转移的关键驱动因素。表观遗传水平的改变可能有利于肿瘤传播和器官定植的表型。
4.肿瘤转移和肿瘤干细胞
肿瘤转移可能由肿瘤转移起始细胞(MICs)驱动的这一概念植根于干细胞生物学。肿瘤干细胞(CSC)假说认为,只有某些细胞才具有启动和增殖(propagate)肿瘤的能力。对白血病、肠癌和其他癌症的研究表明,肿瘤起始CSCs一些具有获得性致癌突变的稳态干细胞。原则上,CSCs可以通过激活一组额外的促转移的基因而直接成为MICs,同时保持其原有的干细胞表型。
事实上,转移性病变经常和原发肿瘤的组织学很相似,因此其分化轨迹也是如此。然而,来自结直肠癌(CRC)研究的实验证据表明,MICs的表型与CSCs不同,更类似于再生祖细胞,而不是稳态干细胞。
5.转移与表型可塑性
MIC具有明显的表型可塑性,并经历了动态的表型变化(图2)。例如,在大肠癌中,对肠道干细胞增殖至关重要的WNT信号通路过度激活的突变会将肠道LGR5+细胞转变为肿瘤起始CSCs(关于WNT信号通路,我们有在《》的综述里详细介绍)。虽然肿瘤是由LGR5+细胞启动的,但在小鼠模型中,从原发肿瘤侵袭前沿扩散、在血液中循环和种植到肝转移的细胞主要是LGR5阴性细胞。一旦在肝脏中建立,一些增殖的转移细胞会在继续建立大转移集落的过程中重新获得LGR5的表达。
关于可塑性在转移中的作用的研究来自对表达L1CAM的MIC研究,L1CAM是一种细胞粘附分子,其在原发肿瘤中的表达与许多癌症类型的不良预后有关。L1CAM在损伤后由肠道祖细胞表达,是上皮再生所必需的。在浸润性肿瘤中,上皮结构的解离会诱导恶性前体细胞产生有高度可塑性的再生表型,使其具有迁移、逃避失巢凋亡和L1CAM依赖的生长再启动的能力。在来自大肠癌、肺癌、乳腺癌和肾癌的转移细胞中,L1CAM的表达介导了在脑、肺、肝和骨髓中转移性生长的启动,因此,L1CAM阳性的MICs具有再生祖细胞(progenitors)的表型,这些细胞在上皮完整性破坏后出现,并推动肿瘤作为转移瘤的远处再生(图2)。
6.上皮间充质转化
另一个与转移相关的表型可塑性过程是上皮-间充质转化(EMT),在EMT过程中,上皮细胞失去极性和细胞间粘附,迁移并侵入基质生成组织。EMT发生在原肠形成、其他一些发育事件和伤口愈合过程中,它经常涉及间质和上皮端点之间的“部分EMT”状态的连续体。具有EMT特征的细胞存在于肿瘤的侵袭前沿,EMT使癌细胞能够迁移、侵袭和转移扩散(图1)。在转移部位,癌细胞经历间充质-上皮转化(MET)这一反向过程,作为开始转移生长的一个步骤。EMT是由上皮基因的SNAIL和ZEB转录抑制因子驱动的。TGF-β与其他通路,特别是RAS-MAPK信号通路协同作用,是子宫内膜上皮细胞转化的有效诱导因子。
这些关于再生祖细胞及其表型可塑性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多阶段的过程,反映了在肿瘤转移中再次发生的上皮修复(图2)。这种谱系(lineage)可塑性通常在侵袭性很强的终末期转移性肿瘤中被发现,并与对标准的组织谱系特异性治疗的抵抗有关。因此,了解可塑性的机制和功能对于提高癌症治疗水平至关重要。
7.循环肿瘤细胞
癌细胞通过侵入血管和淋巴管从肿瘤中扩散出去(图1)。皮肤黑色素瘤细胞也可以通过在淋巴管的腔面上迁移而分散,这种现象被称为血管外迁移转移。沿神经迁移的癌细胞发生神经周侵袭也已有文献记载,然而,血源性扩散被认为是转移到远处器官的主要形式。血液循环中的癌细胞,被称为循环肿瘤细胞(CTCs),是目前研究的热点之一。CTC表达祖细胞和EMT标记,表明这些细胞已经准备好作为转移性肿瘤生长。
对CTC的研究为研究正在进行种子转移的癌细胞的生物学特征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CTC在循环中的半衰期很短,在切除原发肿瘤后基本消失。绝大多数的CTC都被消除了,永远不会形成转移。一些CTC在原发肿瘤消除后仍持续存在或再次出现可能反映了活动性转移灶的存在。因此,治疗仍然需要靶向那些已经在远处器官中定植的转移细胞。
在未经治疗的局部疾病患者中检测到CTC可能有助于识别亚临床转移的患者,潜在地避免了对这些患者进行不太可能治愈或更积极的侵入性手术治疗。特定的分子特征可以识别具有更大最终转移复发倾向的CTC,因此可以作为临床相关的生物标志物。在这一点上,值得注意的是,癌细胞既可以单独流动,也可以成簇流动,在实验模型中,CTC簇具有更好的播种转移能力。CTC簇富集了可表示干细胞状态的基因组甲基化模式。干细胞样癌细胞种植转移是因为形成了簇,还是因为它们是干样才形成簇和种植转移,这一点还有待确定。
虽然目前CTC检测分析的灵敏度仍然有限,但CTC和肿瘤细胞游离DNA(cfDNA)检测技术的改进使早期检测成为可能,并有可能指导转移性复发的早期治疗。相比之下,已确诊的转移性疾病患者的CTC和cfDNA负荷通常比目前的检测方法容易检测到的高,这有助于对治疗反应和耐药肿瘤亚克隆的出现进行连续的非侵入性“液体活检”监测。重要的是,与单个肿瘤的组织活检不同,液体活检整合了来自多个空间离散的转移肿瘤的信息,可捕捉到肿瘤间的异质性,并最大限度地增加了检测到亚克隆耐药相关突变的机会。
8.保护性休眠
在许多癌症中,手术切除原发肿瘤之后几个月到几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现疾病存在的临床证据,但最终仍伴随着隐匿性转移的侵袭性生长(图1)。在原发肿瘤切除前扩散的MIC可以保持处于潜伏期,在休眠和增殖状态之间保持动态波动,直到条件允许这些细胞逃避免疫系统的清除,并随着转移性爆发而生长。人们认为这其中有两种机制:
一种是细胞休眠,即播散性癌细胞进入增殖静止期但不能形成集落;
另一种是肿瘤块(mass)休眠,即肿瘤生长由于不能激活血管生成或与宿主基质所施加的其他约束处于平衡状态而受到限制。
在转移小鼠模型中,播散性癌细胞通常位于毛细血管附近,在那里它们进入生长停滞。TGF-β是一种强有力的上皮祖细胞生长抑制因子,存在于血管周围,可抑制播散性癌细胞的生长。虽然转移性休眠通常归因于基质生长抑制信号对MICs的影响,MICs也可以主动抑制局部促生长信号以进入静止状态,从而保护MICs免受免疫监视。免疫系统与转移性休眠的相关性可以从免疫抑制的器官接受者在移植了被认为已治愈黑色素瘤的捐赠者的器官后发生转移的案例中清楚地看到。
9.建立生态位
正常的成体干细胞依赖于平衡其增殖、自我更新和分化的信号。这些信号是通过与邻近细胞、细胞外基质和扩散因子的接触来提供的,这些因素共同形成了被称为“干细胞生态位”的局部组织结构或成分。播散性转移细胞的存活、静止和爆发同样依赖于基质信号、细胞接触、细胞外基质和代谢信号,统称为转移生态位。MIC和它们的生态位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双向的,癌细胞衍生的因子使宿主组织更有利于MIC的存活。
播散性癌细胞最初在宿主组织中是受排斥的(unw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