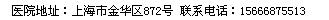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淋巴管瘤 > 患病危害 > ADC药物研发故事肿瘤化疗时代的困惑
ADC药物研发故事肿瘤化疗时代的困惑
北京治疗白癜风哪家医院好一点 https://wapyyk.39.net/hospital/89ac7_labs.html
前言
人们一直致力于研究有效的治疗药物或手段以对抗肿瘤这一威胁人类健康的罪恶杀手。据WHO全球癌症报告[1]:全球乳腺癌新发病例高达万例,超过了肺癌的万例,跃居成为全球第一大癌种。以新晋头号杀手乳腺癌为例,目前已有手术、放疗、化疗、内分泌治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等多种治疗方案。而化疗作为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一直备受重视。
01化疗的发展史
20世纪初
德国化学家PaulEhrlich创造了化学疗法这个词并将其定义为使用化学物质治疗疾病[2]。而化学疗法的现代应用是在20世纪中期由氮芥引入的,年,Goodman和Gilman等应用氮芥治疗一例非霍奇金淋巴瘤和严重气道阻塞的患者,患者肿瘤明显缩小,病情得到缓解,自此开启了化学药物治疗肿瘤的时代[2-4]。
年
SidneyFarber应用叶酸拮抗剂治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虽然产生了严重的毒性反应,但却第一次达到了真正意义的临床缓解[5]。同年Hitchings和Elion两位学者发现二氨基嘌呤在体内可抑制白血病细胞的生长,但毒性太大不宜用于临床。直到年发现6-硫喹和6-巯基嘌呤对动物移植瘤抑制作用最强,并在后续治疗儿童急性白血病取得满意疗效[6,7]。20世纪50年代初,CharlesHeidelberger及其团队合成了5-氟尿嘧啶(5-Fu),该药物被证实对一系列实体肿瘤具有广谱活性,年这一重大发现发表在Nature杂志[2,8]。
年
李敏求证实了单独使用甲氨蝶呤可以治愈绒毛膜细胞癌,绒毛膜细胞癌也成为第一个可被化疗治愈的恶性肿瘤[9]。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抗生素类抗肿瘤药物在儿童肿瘤中得到了广泛应用[10],并引发了研究者探索更有效的抗肿瘤抗生素的兴趣。这些事件共同见证了抗代谢类化疗药物的开枝散叶。
20世纪60年代
研究者发现了长春花生物碱的活性,并且Brunner、Young和DeVita及其同事发现碘苄嗪对霍奇金淋巴瘤具有活性,使得白血病和霍奇金淋巴瘤的治疗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并且一直到70年代初,氮芥+长春新碱+甲氨蝶呤+泼尼松(MOMP)和氮芥+长春新碱+甲苄肼+泼尼松(MOPP)等联合化疗方案对治愈儿童急性白血病和晚期霍奇金淋巴瘤显示出惊人疗效,克服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对药物治愈晚期癌症能力的悲观情绪,促进了辅助化疗的研究[2,11]。
20世纪60年代
顺铂的抗肿瘤效应被挖掘[12],并于年经FDA批准治疗卵巢癌。目前,虽然铂类药物已经发展到第三代,但每一代铂类药物因其独特的药理作用,在肿瘤化疗中均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20世纪60年代
MonroeWall和MansukhWani从短叶红豆杉的树皮中分离出一种具有抗肿瘤活性的化合物。年,这种天然物质被证实为紫杉醇[13]。年,紫杉醇正式被FDA批准用于治疗晚期卵巢癌。随着临床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紫杉醇的适应证也在不断扩充。
20世纪90年代
研究者们相继开发了托莫昔单抗和利妥昔单抗等一系列CD20单克隆抗体,其中,利妥昔单抗于年被FDA批准治疗难治性/复发性CD20阳性的B细胞型非霍奇金淋巴瘤,开启了单克隆抗体治疗恶性肿瘤的新篇章[14]。虽然单克隆抗体本身不是化疗,但是与化疗联用可以增强其疗效,是常见肿瘤化疗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2]。
20世纪90年代
研究者发现伊马替尼具有强大的抗白血病活性[15]。年FDA正式批准伊马替尼用于慢性髓系白血病的进展期(BP和AP)和干扰素治疗后失败的慢性期(CP)治疗。分子靶向治疗就此进入小分子化合物时代。
进入21世纪
以VEGF/VEGFR、EGF/EGFR、Met/ALK/ROS、PARP、PD-1/PD-L1等信号通路为靶点的分子靶向药物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由于化疗药物与分子靶向药物的联合应用,以及个体化用药,标志着化疗从“地毯式轰炸”向“精确打击”迈进。
图1-2:化疗的发展史
02化疗的优势
化疗药物种类繁多,其作用机制各不相同,但细胞毒性化疗药物都是通过影响DNA、mRNA、蛋白质的合成或者干扰细胞的有丝分裂来发挥作用,根据药物的作用点不同,可以将其主要作用机制归纳为:
1.阻碍脱氧核苷酸合成,干扰DNA合成;
2.通过烷化作用与DNA交叉联结,破坏DNA结构与功能;
3.干扰核酸合成中的转录过程,阻碍RNA合成;
4.抑制拓扑异构酶,影响DNA合成,引起DNA断裂;
5.抑制微管蛋白聚合,损伤纺锤体,使有丝分裂停滞[16]。
化疗是一种能普遍适用于各类癌症的全身治疗方法,针对转移性扩散或在局部/远处出现的复发性病灶也能发挥较好疗效,相比手术和放疗只能局部应用展现出绝佳优势。化疗的最佳反应通常是显著缩小肿瘤体积,从而给患者带来生存时间和/或症状控制方面的显著获益[17]。
抗生素类抗癌药和烷化剂化疗药物的疗效和药物剂量显著相关,研究表明化疗药物对特定肿瘤越有效,其剂量-反应曲线越陡峭,药物剂量调整对疗效的影响也会越大。若化疗是出于治愈的目的,剂量降低也会伴随着治愈率和无复发生存率的降低,反过来,若在一定剂量范围内,增加化疗药物的剂量,其疗效也会相应增加[18]。
03化疗的局限性
化疗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治疗方案,其缺点在于化疗缺乏对正常细胞和肿瘤细胞的选择性。药物的毒副反应限制了治疗强度和频率,而大多数常规化疗药物的治疗剂量和中毒剂量接近,具有明显的剂量限制性毒性。化疗不仅损害心、肝、肺、肾、骨髓等重要器官的功能,而且破坏免疫系统,导致机体对肿瘤的自我保护屏障丧失。此外,化疗加剧肿瘤细胞基因组的不稳定性,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迅速产生适应性。因此,化疗的毒副反应和肿瘤的耐药性使大多数肿瘤患者的治疗难以长期持续[17,19]。
04化疗的发展方向与展望
纵观化疗药物70年的发展史,虽然没能彻底战胜癌症,但化疗却不断从姑息性向根治性方向迈进,让众多接受规范化治疗的癌症患者病情得到缓解,生存时间显著延长。尽管作为恶性肿瘤治疗的“三驾马车”之一,化疗的作用极为重要且不可替代,但不可否认众多化疗药物治疗指数小(最大耐受剂量/最小有效剂量[MTD/MED])且同时靶向正常细胞和癌细胞,导致化疗存在严重不良反应,限制了化疗的使用[20]。因此,如何探索更为优化的化疗方案一直是肿瘤治疗领域的研究热点。
在化疗的优化探索道路上,研究者们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了多项临床研究。多年来,紫杉类药物剂量密集方案逐渐成为乳腺癌术后辅助化疗领域的研究热点,如CALGB-研究[21]证实含紫杉醇的2周剂量密集方案较3周标准方案用于腋窝淋巴结阳性早期乳腺癌的辅助化疗,显著改善了患者的无疾病生存期(DFS)和总生存期(OS)。剂量密集化疗即剂量不变而缩短给药间隔,尽管每2周或更短时间给药可以最大程度地杀伤肿瘤细胞,但是这种治疗模式也存在局限性。如NSABPB38研究[22]显示,无论是对于整体人群还是各亚组患者,多西他赛+多柔比星+环磷酰胺(TAC)与剂量密集方案AC4疗程后序贯密集方案紫杉醇(AC-P)这一最强密集方案相比,DFS和OS未见显著性差异。并且在安全性方面,《中国紫杉类药物剂量密集化疗方案临床应用专家共识》[23]指出,紫杉类剂量密集方案会增加骨髓抑制、神经毒性等不良风险,因此紫杉类剂量密集方案的临床应用不仅要注意患者人群的选择,同时要平衡疗效与安全性。
为了规避化疗毒性的局限性,节拍化疗受到了研究者的青睐。SYSUCC-研究[24]探讨三阴性乳腺癌标准治疗结束之后的患者接受卡培他滨节拍化疗的效果,结果表明卡培他滨节拍化疗显示出一定的抗肿瘤活性,该研究也是迄今为止第一项将节拍维持治疗用于辅助治疗并且得出阳性结果的Ⅲ期临床试验。需要更多的临床试验去做进一步的验证。
可见,通过密集化疗、节拍化疗等治疗模式的改变来提高化疗的疗效仍然差强人意,研究者又另辟蹊径,探索了创新作用机制的化疗药物,如艾立布林是具有独特的非紫杉烷型微管作用机制的新型化疗药物,研究[25]证实与常规医生选择方案(TPC)相比,艾立布林能显著提升患者OS,这一惊艳成果也巩固了化疗在乳腺癌中的治疗地位。然而单药化疗很难实现治愈,尽管癌症可能来自单个突变细胞的克隆性扩增,但大多数肿瘤在检测时已经获得多克隆特性[17]。并且大多数抗癌药物使用时,必须接近MTD才能获得具有临床意义的治疗效果。因此,研究者认识到具有非重叠毒性和不同作用机制的抗肿瘤药物通常可以全剂量联合使用,从而产生相加或协同作用以提高抗肿瘤活性,至此引入药物联合的概念,这成为癌症化疗的重要里程碑事件[26]。随着乳腺癌“精准治疗”序幕的拉开,目前在化疗联合分子靶向药物治疗上进行了很多探索,如IMpassion研究[27]应用阿替利珠单抗联合白蛋白紫杉醇一线治疗晚期三阴性乳腺癌,PD-L1阳性患者具有显著的无进展生存期(PFS)和OS获益,基于此研究结果,年,FDA批准该联合方案用于PD-L1阳性晚期三阴性乳腺癌的一线治疗。Keynote临床试验进一步证实了免疫治疗在三阴性乳腺癌中的价值,但IMpassion研究的阴性结果提示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转化性研究,去发现真正获益的人群。不可否认,目前多药物治疗已经成为大多数癌症的标准治疗方式,然而联合细胞毒性药物给宿主带来的全身毒性仍然是癌症治疗的主要缺点,而且仅可能治愈一小部分癌症患者。
抗癌药的临床疗效有限,无论是单药使用还是联合使用,都可归因于这些药物的治疗窗口不足,即无法在不引起毒性的情况下杀死足够数量的癌细胞[26]。据估计,必须杀死超过99%的肿瘤细胞,患者才能达到完全缓解(CR),而根除肿瘤所需的细胞杀伤力要大得多[28]。为了提高抗癌药物的治疗指数,需要提高细胞毒性药物的治疗效力以降低MED,或者改善对肿瘤细胞的选择性以提高MTD。理想的解决方案是开发既能降低最小有效剂量(MED)又能提高最大耐受剂量(MTD)的药物,从而提高癌症药物的总体治疗指数[26]。
ADC药物是一类由抗体、连接头(linker)和细胞毒性药物组成的靶向生物制剂,旨在通过特定的连接头将靶标特异性的单克隆抗体与高杀伤性的细胞毒性药物偶联起来[29]。它结合了单克隆抗体的靶向能力、高选择性、稳定性以及负载药物所具备的高效抗癌潜力,能精准区分正常细胞和肿瘤细胞,将细胞毒性药物靶向递送至肿瘤细胞内。与传统化疗相比,这种免疫偶联剂可以减少细胞毒性药物的全身暴露,从而减少毒副作用,提高负载药物有效性,导致MED降低,MTD增加,从而提高化疗药物的治疗指数[20]。
作为一类具有独特作用机制的抗肿瘤创新药物,既往的临床数据显示,ADC药物在肿瘤治疗中具有很好的疗效和安全性。截至目前,已有8种ADC药物在全球范围内获批用于临床,其中,我国已有2种ADC药物获得批准使用[29],并且新一代ADC药物的代表—DS在其重磅级研究Destiny-Breast01Ⅱ期临床试验[30]中,针对T-DM1耐药/难治性的HER2阳性不可切除和(或)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之前接受治疗的中位线数为6线),ORR可高达60.9%(11例患者达到CR),DCR高达97.3%,中位缓解时间长达14.8个月,中位PFS长达16.4个月,数据令人惊叹。基于其突破性疗效,DS的早日获批上市非常值得期待。相信未来以DS为代表的ADC药物将会拾级而上,将化疗的高效优势发挥极致,并不断克服毒副作用大的局限性,让肿瘤化疗时代的困惑愈来愈少,让肿瘤化疗的应用道路愈加宽阔。
专家介绍
胡夕春教授
医院肿瘤内科主任
临床试验机构常务副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
ESMO乳腺癌FacultyMember
ABC5panelist
中国抗癌协会多原发和不明原发肿瘤专委会主委中华医学会肿瘤分会肿瘤内科专委会副主委
上海市化疗质控中心主任
医院学会乳腺专委会副主委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委会常委兼秘书长
上海抗癌协会癌症康复和姑息治疗专委会主委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评中心审评专家
参考文献:[1]SungH,FerlayJ,SiegelRL,etal.Globalcancerstatistics:GLOBOCANestimatesofincidenceandmortalityworldwidefor36cancersincountries.CACancerJClin.Feb4.
[2]DeVitaVTJr,ChuE.Ahistoryofcancerchemotherapy.CancerRes.Nov1;68(21):-53.
[3]GoodmanLS,WintrobeMM,DameshekW,etal.Nitrogenmustardtherapy:useofmethyl-bis(h-chloroethyl)aminehydrochlorideandtris(h-chloroethyl)aminehydrochlorideforHodgkin’sdisease,lymphos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