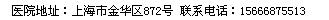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淋巴管瘤 > 优质医院 > 肿瘤干细胞与转移
肿瘤干细胞与转移
作者:张众,王华新,谢丰培
来源: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
肿瘤干细胞(cancerstemcell,CSC)的某些基本生物学性能,如CSC启动和维持癌繁殖的能力,符合最终形成转移所必需的条件,已有实验证明癌干细胞具有转移能力。癌干细胞呈异质性,其中含有具转移能力的亚群。癌巢侵袭性边缘的单个癌细胞可发生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transition,EMT),从而变成CSC状态。对播散性瘤细胞的分析证明其中所含表达CSC的癌细胞比原发灶多。微环境对转移CSC具有重要作用。休眠瘤细胞与CSC有显著的相似性。微环境改变与瘤细胞休眠的起止过程密切相关。
1.概述
据预测,至年全球每年新增癌症患者将近万例,癌相关死亡者将超过万例。换言之,年1年之内将有超过万人死于癌转移。
肿瘤演进过程从原位肿瘤至转移瘤形成,需经历一个复杂的联串过程,包括:原发(上皮性)瘤细胞丧失细胞间连接与突破基膜,迁徙侵袭间质,进入淋巴道、血道、有的侵入体腔、微血管与神经周围,在流动液体中生存,在适宜的靶器官外渗,适应异地微环境,最终繁殖建群。肿瘤局部侵袭有3个重要过程,包括瘤实质细胞黏着性改变、瘤间质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matrixc,ECM)重构与瘤细胞获得运动性。正常上皮细胞形成具有紧密连接,极向排列,以半桥粒锚着于基膜,含有相关中间丝和整合素的细胞片。侵袭瘤细胞发生黏着性改变,脱离原位,突破基膜,以多细胞或单细胞为单位,入侵间质。某些肿瘤,如小细胞肺癌、恶性黑色素瘤与胰腺癌,呈高度侵袭性与转移性;也有一些肿瘤,如基底细胞癌与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虽具局部侵袭但罕见转移。可见转移并非瘤细胞的固有性质,肿瘤侵袭性不等于转移能力。事实上,肿瘤转移的“准备”过程开始于瘤细胞迁徙侵袭之前。几个研究组发现,一个肿瘤的存在即可激发造血干细胞与间叶干细胞的游动,后二者促进瘤细胞迁徙和转移及建构转移龛。对于大多数癌来说,蛋白质溶解依赖性侵袭破坏围绕其四周的物理性屏障当然有必要,但是,如果一个侵袭性瘤细胞尚不具备成功转移的其它特性,其就不能形成转移。由此可见,转移性与侵袭性并非同义性表型。因此,侵袭不能视为转移联串过程的一个阶段,转移仅指瘤细胞从一个部位播散至另一部位。
年,英国外科医师DeMorgan发表一篇关于转移的论述,认为癌呈线性演进,瘤细胞首先进入淋巴结,然后经血液循环到达远距部位。但近年已有一些临床与实验模型揭示癌转移的多向性过程,巡游的癌细胞也可返回至原发瘤本身,称之为“自我播散”。尚有学者将社会科学的“diaspora(散居者)”一词用于癌转移的细胞,认为癌细胞转移或是主动由原发瘤细胞群体设置的监禁中逃逸,或是被动地从生态改变的家园中被驱逐出来。
许多研究者应用脉管内注入癌细胞的模型探讨转移机制。虽然这类模型能提供瘤细胞在脉管系统中生存、外渗及建群的某些信息,但不清楚这类从人工播散获得的信息是否与活体内肿瘤自发转移瘤细胞的生存、外渗及建群相关。非自然转移模型显然不能复制活体自然转移的所有联串阶段,就有可能给疾病演进的机制提供错误信息。年Seyfried等发现CT-2A小鼠胶质瘤在体外具有侵袭性,但在活体内生长则并不发生广泛侵袭或转移。这至少提示生存在不同环境中的瘤细胞,其生物学行为或有所不同。关于转移癌细胞的来源有突变说或克隆演进说、癌干细胞说及细胞融合说等。目前,学者们认为肿瘤转移的癌干细胞说与克隆演进说并非彼此排斥,而是互相补充。所谓细胞融合说是有些学者根据实验所见,认为瘤细胞之所以能转移是由于瘤细胞与淋巴样或巨噬细胞融合。该种细胞融合现象是否与转移直接相关,或仅是显示肿瘤的晚期现象,尚有待探讨。
下文综合近年的文献介绍有关“肿瘤干细胞与转移”几个课题的研究进展,包括:转移性肿瘤干细胞(cancerstemcell,CSC)、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transition,EMT)、SDF-1/CXCR4轴、干性瘤细胞播散、微环境对转移瘤形成的影响及肿瘤休眠。
2.转移性CSC
设想CSC为转移性瘤细胞候选者,是依据CSC的某些基本生物学能力符合最终形成转移所必需的条件。首先,只有CSC具有启动和维持癌繁殖的能力。播散的非干性癌细胞不能建群形成转移瘤。其次,侵袭性肿瘤,如结直肠癌灶边缘的CSC可发生EMT,致其游动性增强,易于播散。再次,CSC对于生长因子和其它信号分子不同于原发瘤的迁居地陌生微环境具有更强的适应性。此外,CSC具有端粒酶活跃表达、逃避生长抑制、抵抗凋亡及启动血管生成等多种能力。在考虑转移所经复杂的生态过程时,这些表型特性会得到特别重视。
依据一般所认为的干细胞标记CD44+/CD24-/low,年Liu等分离乳腺癌CSC,将其正位移植后,生成的原发瘤发生肺转移。年Malanchi等将定为CSC的Lin-CD24+CD90+细胞群从小鼠乳腺中分离,进行活体移植,发现其拥有肺转移能力。该类研究证实,原发瘤干细胞群与转移率增高相关。但仍有待阐明CSC与远距转移来源的因果关系,究竟是同一移植CSC群导致原发瘤生长与远距转移?抑或这些过程是由不同CSC细胞亚群完成?这是个必然要提出的问题。
年Dieter等通过分子追踪分析肿瘤起始细胞的组成,发现结肠癌CSC有3种,包括LT-TIC(长期自我更新细胞)、T-TIC(短期扩增细胞)和DC-TIC(延迟促进性细胞,在第2、3代小鼠具有活性),其中LT-TIC是唯一具有转移能力的CSC亚群。年Hermann等报道胰腺癌CD+CSC群中有一个迁徙性CD+CXCR4+亚群,继之该亚群可发生肝转移。CD+CXCR4+亚群呈高度恶性和转移能力。在活体胰腺癌正位模型,可从门静脉循环瘤细胞中最先发现。应用CXCR4受体抑制药物可消除其转移能力。ALDH+CSC较ALDH-癌细胞明显富于转移性。年Croker等用ALDH+和CD44+联合标记,从乳腺癌中筛选出CSC亚群,将其注入尾静脉或正位移植,证实其转移能力增强。仅ALDH+CD44+CD24-细胞能在肺内形成大的转移瘤并向肺外转移至肝、胰、肾、脾。年Pang等鉴定CD26是结肠癌迁徙转移形成CSC的一种标记。晚期结直肠癌的原发和转移瘤中均可检出CD26+细胞亚群,所有转移瘤均含有CD26+细胞,而所分析的原发瘤仅1/3(8/27例)阳性。原发瘤不含CD26+细胞的患者无1例发生转移。在对NODSCID小鼠进行移植试验中将CD26+和CD26-细胞分别注入小鼠盲肠壁后均产生肿瘤,但仅CD26+细胞能从门静脉血中检出,并发生肝转移。原发瘤中存在CD26+细胞预示以后会发生肝转移。以上几组试验结果表明CSC中存在转移能力较强的亚群。年Bacceli等将这类CSC亚群称之为转移性癌干细胞或转移性肿瘤起始细胞。他们认为CSC呈遗传不稳定性。在肿瘤演进早期、晚期或复发的侵袭播散不同阶段CSC克隆由于本身遗传变化与微环境改变,而产生能最终生存建群的新克隆,即转移性CSC或MIC亚群。
2.1EMT
年Brakletz等发现结直肠癌癌巢边缘部单个癌细胞侵袭时可呈与胚胎发育及创伤愈合时相似的EMT。癌细胞由原有极向排列、无运动性上皮表型变为无极向、具有运动性的间叶表型。EMT的关键调控物为TGFβ,其它介导因子包括HGF/SF、PI3激酶通路、MAF激酶、Sprouty4,转录因子有ZEB1、Twist和Snail,信号通路Wnt、Notch与Hedgehog。转录因子Twist等使癌细胞丧失E-cad表达。β-Catenin从细胞膜移位至胞质与胞核。细胞表达FN、vimentin、SMA与N-cad等间叶表型。在丧失EMT诱发信号时,间叶型癌细胞也可发生间质-上皮转化(mesenchymal-epithelialtransition,MET)。
EMT能促使分化细胞变成CSC样状态。EMT细胞与未发生EMT细胞相比,较富于CSC活性。在永久性人类乳腺上皮诱发EMT,在用TGF-β处理和Snail或Twist外源性表达时,可获得CD44highCD24low表型及较大乳腺球形成的细胞群。EMT所产生的间叶表型癌细胞其运动能力与凋亡抵抗性增强,表达MMP,从而更具侵袭性。从正常乳腺和乳腺肿瘤分离的干样细胞也表达EMT标记。CSC表达诱发EMT的转录因子,如Twist、Snail和Slug。
年Tsuji等从单个肿瘤分离出呈EMT改变的Cell-Ⅰ与保持原有上皮形态的Cell-Ⅱ,发现Cell-Ⅰ能侵入血管,但如直接注入血管并不形成转移瘤。Cell-Ⅱ经正位注射不能侵入血管,但如注入血管能转移性建群。如把Cell-Ⅰ和Cell-Ⅱ混合正位注射,所产生的转移瘤中可发现两种细胞成分。结果提示,EMT本身具有侵袭性还不足以成功转移。细胞合作对于转移灶建成起关键作用。由此,更认识到肿瘤异质性的生物学意义。
2.2SDF-1/CXCR4轴
SDF-1/CXCR4轴对于正常干/祖细胞功能、原发癌生长、侵袭和转移必不可少。多种组织特异性干细胞表达CXCR4受体。多种间叶源性细胞,如纤维母细胞、骨母细胞、内皮细胞、造血干/祖细胞产生SDF-1。组织损伤和缺氧时,HIF-1引发CXCR4与SDF-1表达上调。癌干/祖细胞表达的CXCR4受体对间质细胞SDF-1来源的化学吸引物发生反应,致使癌干/祖细胞沿SDF-1浓度梯度呈方向性迁徙,直到癌干/祖细胞抵达和停留于SDF-1高表达的微环境。
3.干性瘤细胞播散
侵袭癌细胞在跨越脉管内皮细胞及微血管管周细胞以后,进入淋巴血液循环,成为播散瘤细胞。此时,其生存是在ECM整合素依赖黏着性被剥夺,而不发生失巢凋亡的基本条件下,必须克服循环流动性液体所致的应力损害,及逃避免疫系统,特别是自然杀伤细胞的捕食。播散瘤细胞可以单个生存或与血小板相互作用形成栓子,存活的播散瘤细胞最终可自微脉管外渗,在适宜的靶器官微环境中生存建群。据文献报道,仅低于0.01%的血液循环瘤细胞可最终成功繁殖成转移瘤。
Balic等和Alix-Panabieres等从早期乳腺癌患者骨髓抽吸物所分离的播散肿瘤细胞(disseminatedtumorcells,DTC)中,发现比原发病变有更多表达CSC的癌细胞(CD44+CD24lowCK19+MUC1-EpCAM-)。年Scatena等设想在一个患者或不同患者体内的外周血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tumorcells,CTCs)表型有3种类型:(1)BystanderCTC,缺乏EMT和(或)CSC特征;(2)pathogenicallyactiveCTCs,具有EMT和(或)CSC特征与形成转移能力;(3)迁徙性CSC或循环性CSC。年Balic等分析临床试验治疗患者DTC中的CSC,所用指标为CD44+CD24-/low,分析结果提示DTC中的大部分细胞呈CSC表型。据报道,该类细胞在原发瘤中所占比率<10%,而在DTC中,作者发现高达72%的肿瘤细胞呈干性表型。年Theodoropoulos等在66.7%乳腺癌患者检出CTC,其中35%CTC具干性表型(35.2%CD44+/CD24-/low及17.7%ALDHhigh/CD24-/low)。年Aktas等分析39例转移性乳腺癌患者的个血样,发现62%的CTC阳性患者至少有3个多重性EMT标记(AKT2、PI3K和Twist1)。62%的EMT阳性CTC患者的62%对姑息性化疗抗体或激素处理无反应,仅10%EMT阳性CTC患者对同样治疗呈阳性反应。年Reuben等用流式细胞筛选法前瞻性分析癌患者骨髓抽吸物,显示高百分率CSC患者具特别高的危险临床病理特点,年Wang等用流式细胞分析,评估不同分期乳腺癌患者外周血癌干细胞,示阳性率随分期增高。Pantel和Alix-Panabias及Hou等报道,从DukesB和DukesC结肠癌所获CTC,表达CD、CEA和CK的患者,由于转移,其预后明显劣于CTC不表达该类标志物的患者。以上几项研究证实了肿瘤DTCs/CTCs中含有相当比例的CSC或EMT细胞。
4.微环境对转移瘤形成的影响
转移瘤的建成将重演类似原发瘤形成时的间质建造过程。下文中以POSTN与TNC为例,说明微环境对转移CSC的重要作用。
Malachi等发现POSTN在正常干细胞龛、原发瘤间质及新形成转移瘤中高表达。POSTN是ECM的一种糖蛋白,在机体发育过程中高表达,成人除干细胞间叶性龛以外,间叶基质的表达均下调,但在人类和小鼠乳腺肿瘤间质的α-SMA+vimentin+纤维母细胞中广泛表达,也沉积于乳腺癌的淋巴结与肺的转移瘤内。敲除POSTN可致小鼠转移明显减少。POSTN可募集和呈递Wnt配体于瘤细胞,增强CSC的WNT信号,这对于保持干细胞的特性非常重要。
年Oskarsoon报道,乳腺癌肺转移瘤细胞首次到达肺形成微转移时,产生和分泌成功转移所需的TNC。当微转移继续增长过程,则由活化纤维母细胞与肌纤维母细胞产生TNC。TNC增强瘤细胞的Wnt与Notch信号及对异地微环境的适应性与生存优势,从而促进转移瘤扩增。年Oconnell等发现,S-A+肺纤维母细胞由于浸润性瘤细胞的出现而发生增生反应,分泌VEGF-A和TNC,以支持转移建群。消除这种纤维母细胞群可降低TNC表达水平和削弱转移瘤增长趋势。
4.1转移龛
转移龛一词用以表达播散瘤细胞异位生存建群所必需的微环境,即年Paget在其“种子与土壤”学说中所指的土壤。转移龛常位于微血管周围,在此,有ECM重建,新ECM成分沉积,所涉及的分子包括FN、TNC、POSTN和versican;参与改建的其它因子有Fibulin、MMP-9、MMP-2、LOX、LOXL、HIF等。转移龛细胞成分中有几种BMDC(骨髓源细胞),表达VEGFR-1的造血祖细胞、炎细胞与免疫细胞(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B淋巴细胞、T淋巴细胞、NK细胞)、纤维母细胞(包括CAF)、血管与淋巴管内皮细胞。血管重建是龛的重要变化。转移龛的功能包括诸如吸引CTC和刺激其外渗,建立转移瘤细胞繁殖所需的炎性环境,产生生长因子、细胞因子与趋化因子等,调控转移瘤细胞干性,EMT与休眠状态。位于微血管周围的转移龛可启动和保持CSC特性,使非CSC获得干性表型。转移龛ECM成分,如POSTN可促进EMT。
4.2缺氧效应
人体细胞需要充分氧供,以使线粒体持续产生ATP。氧的递送与消耗经缺氧诱发因子(hypoxia-induciblefactors,HIFs)活性准确调控。细胞增生时,氧耗增多可致缺氧,从而激活HIF,增加VEGF基因转录、血管增生,以增强氧供。癌以细胞增生失控为特性。实体瘤内新建血管经常结构异常,因而瘤内常发生严重缺氧与HIF活化,如此,促进血管增生,激活生长信号,重编代谢程序,维持干细胞,促进EMT与癌的侵袭、转移能力及对放、化疗的抵抗性。缺氧不仅对肿瘤的演进具有重要影响,也诱发和调控转移龛形成因子,如VEGF-A、PIGF和LOX的表达,上调SDF1-α,蓄积VEGFR1+CD11b+骨髓源细胞,参与“前转移龛”的建立及促进炎性微环境形成,以支持转移灶的增长。龛能保持正常干细胞的未分化状态,维持CSC的干性特性。
4.3前转移龛
年Kaplan等研究VEGFR1+VLA4+骨髓源树突状细胞(bonemarrow-deriveddendriticcells,BMDC)参与恶性黑色素瘤肺转移的“前转移龛”建立过程。他们结合流式细胞计和绿色免疫荧光蛋白标记技术,显示预定转移器官在荧光标记瘤细胞抵达前即可检出VEGFR1+VLA4+BMDC群聚。这些BMDC表达CD34、CD11b、c-Kit和Sca-1,表明其为早期造血祖细胞。VLA-4帮助选定富于配体FN的部位建立“前转移龛”。瘤细胞分泌PIGF(VEGFα1配体),激活纤维母细胞合成FN,FN诱发VLA-4+造血祖细胞集聚,后者分泌趋化因子、生长因子和黏着因子为抵达的瘤细胞建成适宜的“前转移龛”。瘤细胞来源的exosomes可调
节骨髓造血祖细胞表达MET(受体酪氨酸激酶)。MET激活HGF,加强骨髓细胞迁移性。在缺氧条件下,乳腺癌细胞分泌LOX。在ECM中聚集的LOX与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交联时,对“前转移龛”的诱发也发挥一定作用。CD11b+BMDC聚集于Ⅳ型胶原,产生MMP2,分裂胶原,有利于BMDC和瘤细胞入侵。其它如瘤细胞分泌的IL6和IL10、VEGF-A、TGFβ、S-A8和S-A9等都参与“前转移龛”的形成。
4.4转移的器官选择性
各种恶性实体瘤复发转移均有其各自倾向的部位,如:乳腺癌转移至骨、肺、肝、肠;肺腺癌转移至脑、骨、肾上腺、肝;皮肤黑色素瘤转移至肺、脑、皮、肝;结直肠癌转移至肝、肺;胰腺癌转移至肝、肺;前列腺癌转移至骨;肉瘤转移至肺;葡萄膜黑色素瘤转移至肝。播散瘤细胞的遗传性或表遗传性变化,微环境的系统性或局部性改变,或这些因素的联合,最终不仅赋予存活播散瘤细胞建群的充分能力,而且在宿主不同器官微环境特异性应力选择下,产生不同生存特性的转移瘤细胞,它们在同一患者选择不同器官建群。已有文献报道:受某些基因管控的转移器官亲和性,包括骨、肺、脑与肝。例如研究结果揭示,骨源性趋化因子Osteopotion、Osteonection和间叶源性因子1(SDF-1即CXCL12)在乳腺癌和前列腺癌骨迁徙过程发挥作用。PTHrP在乳腺癌转移的骨破坏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而非骨器官转移仅17%表达这种蛋白。
5.肿瘤休眠
肿瘤休眠是指瘤细胞演进的延缓阶段,在此过程单个瘤细胞或微小瘤细胞群保持潜伏性,虽无生长迹象,但保存恶性演进能力的状态。肿瘤休眠可发生于肿瘤播散转移过程。有些类型癌的播散瘤细胞,休眠可达10年之久。例如乳腺癌骨转移,休眠瘤细胞可呈单个或微转移灶存在。肿瘤休眠期的细胞周期停顿于G0/G1期,缺乏增生与凋亡活动,但保有荧光示踪物。
对休眠瘤细胞群生物学特征的了解,受限于可靠生物学标志物和缺乏充分的细胞分离技术。近年来,由于认识到休眠瘤细胞与CSC的显著相似性,有学者开始从具有特异性生物标记与免疫生物功能的CSC所获启示,来探索休眠瘤细胞的本质及其调控机制。
休眠瘤细胞与CSC在概念上有惊人的相似性,如:二者均为创始肿瘤的自我更新细胞亚群;在一定时期内休眠瘤细胞在增生和凋亡间保持平衡,既不死亡也不繁殖,经长期静息后,终可复发及转移;休眠瘤细胞像CSC那样,能在细胞毒治疗过程与供养较差的微环境中生存;二者均抵抗标准的化疗、放疗;许多涉及控制肿瘤休眠状态的生物学机制也控制CSC的行为,包括细胞周期更改、血管生成过程及抗肿瘤免疫反应调整;微环境信号、血管生成因子与免疫监控因素均控制肿瘤休眠状态与CSC的命运。
目前尚不了解CSC是否发生长期休眠。CSC是由异质性亚群组成,其中包括显著静息的周期缓慢细胞,推测可能存在呈休眠状态的CSC亚群。年Haraguchi等发现肝细胞的半休眠癌引发剂,为肿瘤休眠与CSC的直接关联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他们的研究显示,肝CSC中存在一个具有缓慢周期特性的亚群。
瘤细胞休眠与微环境的调节相关,CSC信号和龛相互作用可能控制肿瘤休眠状态。P38-MAPK信号激活可使前列腺CSC进入肿瘤休眠,MYC灭活引起不同肿瘤细胞老化。调控CSC静息与肿瘤休眠的信号网络包括Sonichedgehog、Notch和Wnt/β-Catenin。微环境的TGF-β能激发CSC的不成熟性与维持肿瘤休眠,特别是TGF-β2和TGF-β3是休眠癌细胞与CSC不可或缺的伴随者。微环境血管生成因子及免疫逃逸与排斥间平衡的建立,对于开启肿瘤休眠具有关键作用。缺氧、具有细胞抑制性的CD8+T细胞,均可诱发休眠。p21活化诱发肿瘤细胞休眠,龛内DTC诱发EMT时,由于增加p16ink4a,抑制CyclinD表达,也可使细胞增生中止。
瘤细胞从休眠状态转变为增生状态的大部分机制仍不清楚。微环境成分改变可使DTCs中止休眠。例如,通过Ⅰ型胶原沉积,改变ECM成分可使瘤细胞休眠解除。uPAR激活β1整合素,使其能与FN作用,而致瘤细胞中止休眠。血管生成可解除血管生成性休眠。意外事件中,细胞因子的改变可解除CD4+T细胞诱发的休眠。CSC免疫生物学通路信息改变可能在肿瘤休眠变为急剧细胞增殖中担负重要作用。总之,微环境的改变与瘤细胞休眠的起止密切相关。
6.结语
癌转移的研究结果显示:
(1)癌转移可能源于癌干细胞;
(2)肿瘤的组成具有异质性,CSC也含有不同的亚群,包括转移性CSC;
(3)CSC具有可塑性与动态性;
(4)肿瘤转移的形成与微环境变化关系密切。
以上几点提示在诊治肿瘤转移时应考虑的基本对策:
(1)主攻方向是播散性CSC,若果真存在休眠性CSC,如何识别并消灭之,是应予攻克的课题;
(2)在治疗过程中,不可忽略关于肿瘤异质性,非CSC群,特别是针对治疗抵抗性亚群和转移瘤细胞微环境的综合治疗;
(3)针对CSC的动态性,应动态性地对肿瘤患者进行个性化诊断与治疗。
参考文献(略)
加入QQ群,与更多病理朋友同行:
91智慧病理网(91.
91病理论坛(bbs.91.小儿白癜风能治好吗治疗白癜风哪家医院比较好